梁秋虹 ╳ 謝金魚 ╳ 吳曉樂《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座談側記
本篇文章以2025年9月20日於台南政大書城舉辦的「誰在算計女人的命運?——從《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談台灣女性生育自主權百年史」座談會為底,經簡單調整、編輯後刊出。
感謝為台灣墮胎史留下重要詞條的吳燕秋博士、講者梁秋虹老師與謝金魚作家、當天參與的聽眾,以及從這本書出版以來就持續送上祝福與愛的許多人。
吳曉樂: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幫我們完成歷史篇的梁秋虹教授,還有歷史作家謝金魚。《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除了邀請作家、藝術家進行文學方面的表達,也找了法律專長的陳宜倩教授告訴我們,為什麼台灣此時此刻還會有墮胎罪。另外我們覺得歷史觀點也很重要,就是華人長期以來是如何看待女人肚子內的胚胎。而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研究台灣女性墮胎史的開創者就是吳燕秋。可是當我一Google吳燕秋的聯絡方式,第一篇跳出來的文章就是她的告別式訊息,她在2023年底過世了。我們開始思考有沒有可能找別人,可是不管怎麼找,每個人都說沒辦法,因為長期以來以台灣女性為主體的墮胎歷史學研究就是只有她一人。這時候我有一個中研院的朋友傳訊息跟我說,這個問題你如果不曉得該怎麼解答,因為你沒有歷史學的人脈跟背景,你可以去找一個人,這個人或許可以告訴你該怎麼做。這個人就是李貞德。這是一個巨大的巧合,因為去年我邀請謝金魚來台中女中演講歷史學的時候,她剛好提到了李貞德老師的《公主之死》。可不可以先麻煩金魚老師跟我們講一下《公主之死》,因為我後來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巧合,這本書談的內容跟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有非常高度的重疊。
公主之死——當漢人駙馬打死鮮卑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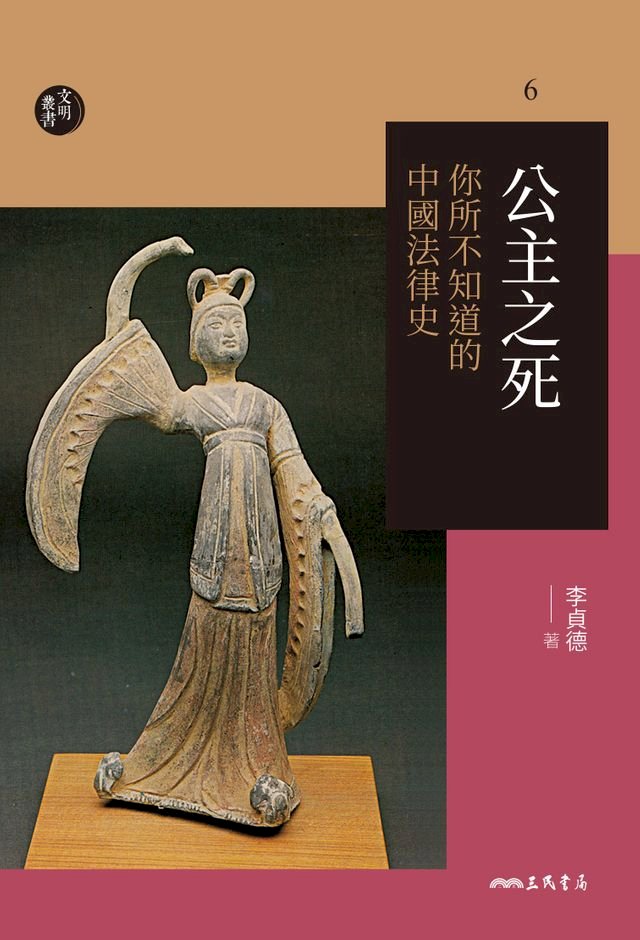
謝金魚:李貞德老師其實一直在研究女性相關的主題,包含生育。古代女性的生育,我們台語常會講「生會過就麻油芳,生袂過就四片板」,你如果生不過的話就是死、見棺材。李貞德老師的研究其實推到更早期,中國中古北朝到隋唐之間,老師當年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就是北朝的蘭陵公主,北魏孝文帝的女兒。大家會想像公主沒有什麼婆媳跟夫妻問題,應該幸福快樂美滿,可是這個公主的人生有點悲慘。她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所以是她哥哥、嫂嫂,就是後來的胡太后把她拉拔長大。她長大之後就許配給了她先生,南朝皇室的後代,兩個人一開始也不錯,可是這個先生是個渣男,一直在外面搞小三。公主很生氣,想說我貴為一國公主,你吃我的喝我的,住在我們家,還給我搞小三。她對小三進行了其實滿殘忍的報復,駙馬也無法忍受,所以兩個人就離婚了。但過了幾年之後,公主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又跟太后說兩人願意復合。所有人都勸她不要,可是公主就很堅持。
兩人復合之後,公主竟然很快就懷孕,那時候公主已經三十幾歲,在當時算是高齡產婦了。沒想到此時駙馬又再出去搞小三,而且不只搞一個,他搞兩個。公主當然非常生氣,那時候她應該已經接近臨盆了。當時睡覺有一個比較高的床具,像一個台子,公主可能睡到一半突然覺得忍不了這口氣,兩人開始吵架,然後這個駙馬就揍公主,揍完之後把她推到床下,公主就受傷,可能有流血。駙馬一看狀況不對勁,第一件事情不是去叫醫生,而是帶著他所有的家私(ke-si)逃跑了。等到皇太后發現這件事情去救公主時,小孩已經流掉了,公主後來因為傷重也過世了。
當時的太后覺得我一定要替小姑出這口氣,太后跟漢人官僚之間就產生了巨大的分歧,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就是法律怎麼介入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法律怎麼介入生育?法律怎麼介入家庭問題?不要以為法律都跟我無關,不,法律會像張網,天羅地網把你牢牢罩住。太后就說我要殺駙馬,你想辦法去給我生一條法律,我要把他處死。太后這邊北朝的法律官僚就說那不如這樣,因為是駙馬打公主,公主懷孕流產就是傷了這個胎兒,這個胎兒是公主的小孩,就是我們皇家的後代,這樣的話駙馬就是以臣犯君,以臣下身分打死了皇室的後代,所以是以下犯上,罪加一等,這個駙馬應該處死。
這時候的北朝是二元體制,一方面有漢人官僚在處理很多事情,但上面其實是鮮卑人統治的國家。我要提醒大家,中國史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是由外族統治的朝代,沒有什麼自古以來就是漢人帝國,沒有,如果你是漢人,你有很大的機會跟胡人有關係。總之,漢人官僚就說不是這樣算,那是你們胡人的算法,那是你們鮮卑人的算法,在我們漢人呢,駙馬跟公主就算有臣下跟君主的關係,可是在家庭當中、私領域當中,他們是夫跟妻,丈夫打傷妻子跟不小心打死自己的小孩,是以「上」御「下」,罪減一等,駙馬頂多罰點錢就沒事了。
如果你是太后,你聽到這個說法會怎樣?我當然不會允許。太后就要求動用國家機器,一定要讓這件事情,原本在漢人家庭當中是私領域的丈夫打妻子,不小心打死自己小孩,把這件事情上升到國家領域,成為以臣犯君,打死皇家後代,處死駙馬。在這過程當中,你也可以看到北朝的皇室、法律跟國家制度,怎麼樣因為這些人的私欲而產生了變化。結果簡單跟大家說,公主死掉了,駙馬後來被抓回來,當下判了死刑,但因為北朝後來發生一些事,駙馬並沒有被處死。這條法律的紀錄當中,很明確地討論到如何界定家庭當中的法律,如果你是駙馬這種特殊身分,要被歸類到公領域還是私領域。上對下要罪減一等,下對上要罪加一等這件事情,也在那個時候慢慢確立。
所以剛剛曉樂講的其實非常重要,所有法律、家庭的問題,都跟政治有很密切的關係。在蘭陵公主的案子當中,已經不再是一個男人跟女人之間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法律怎麼去界定這種家暴事件要怎樣處理。你可以在書裡看到這個脈絡,北朝到隋唐到後來的朝代當中,法律當中妻子都是弱勢的一方,丈夫打妻子是理所當然,父親打死兒子有一點問題,就是你幹嘛出手那麼重,可是罪不致死。到現代才開始把孩童、把丈夫跟妻子拉到平等的地位,所以才有家暴的問題。小時候誰沒被爸爸媽媽打過?我們以前是被媽媽的三大神器,雞毛撢子、衣架之類的、水管,跟老師的三大神器之一愛的小手,每個人都被打大的。我們小時候也沒想過要打113家暴專線。現在的小朋友被揍了就會打113,我們小時候沒有這種東西。所以其實法律是與時俱進的,是跟著每個時代人們認為怎樣的概念是對的。落實到今天這本書的主題人工流產,從古代到現在,從中國到台灣,從日本到台灣,它有非常長遠的脈絡,所以到現在我們還存在墮胎罪,我其實覺得滿荒謬的。
吳曉樂:我剛拜託金魚重新講一次《公主之死》的梗概,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跟我們今天討論的東西有非常大的關係。一個女人她本來有自己的身分,可是她在進入婚姻之後,我們漢人的邏輯就會把這個女人間接視為先生的財產。我可以講兩個例子讓大家感受一下。在兩千年以前,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民法》規定,先生可以自由使用妻子的財產。那表示什麼呢?就是我們並不認為妻子擁有自己財產完整的所有權,先生可以直接使用。後來發現到不對啊,為什麼結婚之後夫可以自由處分妻的財產,我們才改變。以前的《民法》還規定,夫妻的住所以夫的住所為原則。所以不久以前,可能我們媽媽那個年代,其實女人一結婚之後,地位會瞬間驟降。
還有一條很可怕的法律,這現在已經沒有了,就是以前並不承認配偶之間有強暴罪、妨害性自主。為什麼?因為我們覺得你如果跟你先生結婚,你不可能不要的,你不可能在性上面說不。以前我們並不承認婚內有妨害性自主的可能性,是之後才發現到不對啊,我跟一個人結婚,原來有這麼多東西,法律已經幫我間接規定了,我不能有意見。所以我們可以去想一下這個公主,她肚內的孩子到底是皇室的成員還是先生的?這個宗族的家族的小孩,到底是誰的?其實我們法律有一個規定,如果已婚女性要進行人工流產、終止妊娠,她要經過配偶的同意。其實這也是預設肚內的孩子不完全是這個女人的,也是她先生的。
謝金魚:我要補充,其實我們《民法》以前有個很荒謬的概念,就是如果夫妻離婚,太太在六個月之內不可以再婚。為什麼?因為怕你帶著前夫的孩子嫁給後夫,混亂了後夫的宗族,所以你必須在六個月之後,確認你沒有懷孕,你才可以結婚。
吳曉樂:後來廢掉了。以前會有這個規定是因為以前沒有DNA鑑定。整個婚姻法的規定,其實都是以男性宗族的利益,不只是男性這個人而已,是以他的家族利益為前提。
那我們再繼續講下去,當時李貞德老師在中研院其實所務繁忙,她回信就寫了「所務繁忙」,我本來心一沉,但往下滑她寫說「但我給你三個選項」,我馬上想說老師也太好了,拒絕我之後給我三個錦囊妙計。她說其中一個方法是,因為我們要使用吳燕秋老師的論文,我們得先去確認她的論文目前的智慧財產權是在誰身上,我們取得此人的同意之後,找到可信賴的人選進行改寫。然後李貞德老師又再給了我們三個改寫人選。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詢問吳老師論文的財產權到底在誰身上,非常高興,就是在她的遺孀伊瑪貓身上。伊瑪貓同時告訴我們,在這三個人選之中,她覺得梁秋虹老師最適合,所以當時秋虹老師應該也無法說不了。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如此大費周章地使用吳燕秋博士的論文進行改寫,因為我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吳老師這麼早就決定要以女性為主體,進行台灣墮胎史的研究?每一個人都跟我說,如果你要了解這個題目,她是不二人選。那既然她是不二人選,無論再怎麼麻煩,我都想要讓她的文章被更多人看見,也是作為紀念,紀念有人在這麼早的時候,就為我們留下這麼多台灣女性的聲音。那我們現在請當初的「不二人選」梁老師,講一下當時突然接獲這個任務的心情,以及你跟吳老師的交情,如何讓這一切落到你手上。
《失落詞詞典》——那些沒有人要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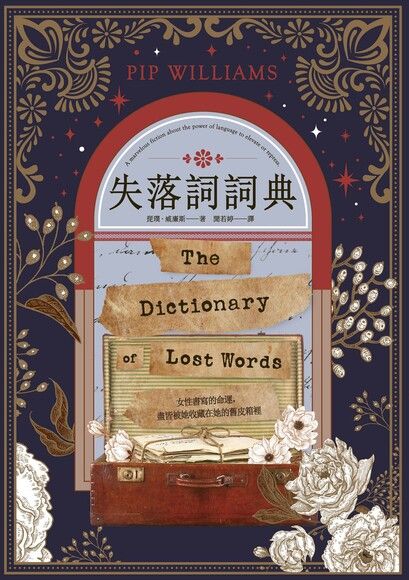
梁秋虹:大家好,我是成大歷史系梁秋虹,我想要用另一個方式來跟大家介紹,用另一本書來介紹這本書。我知道要來參加座談會後,除了回去看我當初改寫的文章外,也看了吳曉樂老師做的關於人工流產經驗的採訪。當我把吳燕秋做的口述歷史跟吳曉樂做的流產者採訪放在一起時,我想起了另一本書《失落詞詞典》(The Dictionary of Lost Words)。它是一本翻譯書,它其實是一本虛構小說,主角的父親就是當初編撰《牛津英語詞典》的人。本書主角是個小女孩,爸爸是個在牛津大學德高望重的學者,那這個小女孩在爸爸身邊做什麼呢?就是在爸爸編詞典的時候,專門把爸爸不要的那些紙條撿起來看。那些紙條就是沒有被收進《牛津英語詞典》裡的詞條,這些詞條的來源,很多是透過讀者來信的方式,其實有一點像曉樂在做的事,就像曉樂在網路上公開徵求受訪者,十九世紀《牛津英語詞典》的做法也是這樣。小女孩在收集那些紙條的時候,她就在想,為什麼這些是不要的聲音?為什麼有一些沒辦法被編進去?
這個世界上應該被語言指認的事物無窮無盡,可畢竟《牛津英語詞典》的篇幅是有限的。小女孩就開始好奇這些聲音是什麼,開始一一去讀垃圾桶裡面的聲音,然後她就發現裡面有好多關於女性的聲音是不會出現、不被承認的。如果說這些聲音沒有被指明,沒有被編寫成詞條,沒有被命名,那它是否還存在呢?小女孩就開始自己去收集這些聲音,去傳統市場問婦人,問各式各樣的婦人、攤販。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她收集到女人在懷孕生產時,因為太痛了所喊出來的髒話,一個髒字。她覺得這個字很傳神,為什麼爸爸不要?她就開始收集這個。《失落詞詞典》就是記錄了詞典編纂學者父親身邊的小女孩,日後也成為語言學教授的故事。
我剛剛說這本書是一本虛構寫作,我們好像以為這裡面大部分都是虛構的,都不是真的,但這本書又在最後告訴你,它的虛構寫作裡承載了多少歷史事實。它針對當初編寫牛津詞典的那個父親,做了非常多的考證,包括他的家人、家人間的關係。我們以為好像很殘忍、很荒謬的事情,其實都是真的,所以它就有一些驚奇在裡面。然後我就覺得,這其實也很像曉樂在做的事情,我後來回去仔細看了曉樂的採訪,她的受訪者平均年齡分布在28歲到60歲之間,針對受訪者的族群、階級、社經地位、教育程度、流產場所,都做了非常多細膩的平衡,以及性別研究所謂的「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然後我就覺得,她們在做的不正是一樣的事情嗎?曉樂在做的其實也是非虛構寫作,她在裡面談了她為什麼要使用化名,因為她某種程度要保護受訪者,什麼東西是她應該說的,什麼是她不應該說的。這就是關於疼痛這件事情,或者說關於這樣子的記憶要如何被保留。
啤酒、啤酒與啤酒——無差別格鬥派的豪爽女人吳燕秋
梁秋虹:吳燕秋是個女性歷史學家,她是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我簡單用三個畫面來介紹她。我認識吳燕秋的時候,我們是中研院的同事,我們很快就一見如故,那時會在一些很正式的場合遇到,但後來我就發現燕秋她其實是一個不那麼嚴肅的人。比如前陣子我的臉書回顧出現了燕秋的照片。2010年前後有很多遊行,有一天我們夜宿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凱道上擺著野餐墊,還有非常多的啤酒,都是吳燕秋帶來的,她是一個非常喜歡喝啤酒的高雄人。大家要知道,其實沒有什麼人會帶啤酒去遊行,畢竟啤酒很重。所以你就知道她其實是個有點野性、很豪爽、不拘小節,然後覺得啤酒比人生很多事情都更重要的一個女人。
第二個畫面也是啤酒。我們一群社會學跟歷史學的女博士約在建國啤酒廠。我記得那篇臉書貼文的重點是,我原本以為只有社會學的人會喝,沒有想到歷史學的人也可以喝成這樣子,重點是那一天我們同桌裡有一位是邱妙津的高中同學,我就覺得哇,於是寫下那篇貼文。可是我事隔多年後發現,其實我已經忘記邱妙津的高中同學是誰了,可是我仍然能夠回想起我跟吳燕秋一起喝酒的畫面,我跟她的記憶一直都離不開啤酒。
最後一件跟啤酒有關的事,就是吳燕秋的告別式。其實我沒有去她的告別式,我提早去會場看她,我一去就遇到她的伴侶伊瑪貓,然後她就看著我,說「你為什麼沒有帶啤酒來?」她說我兩手空空,然後我就說「啤酒很重欸」。後來我走進簡易的靈堂,然後我就發現天啊,桌上有紙紮的啤酒塔,我就覺得哇,你怎麼能不感受到她們伴侶之間那種相愛的關係。
我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伊瑪貓,我為本書寫的歷史篇,篇名叫做〈無差別格鬥派的愛情〉,其實我就是從伊瑪貓跟吳燕秋的故事開始說起。有一天我讀到一篇人物專訪,那篇專訪的主角說她從小的心願就是可以變成《亂馬1/2》的亂馬。《亂馬1/2》是日本漫畫家高橋留美子的名作,亂馬是一個無差別格鬥派的武術家,特色是只要一潑到冷水,就會變成一個辮子姑娘,直接從男性變成女性。而亂馬的爸爸只要被潑到冷水,就會從武鬥家變成大熊貓,漫畫裡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樣的變身。這是我們從小就很熟悉的漫畫文本,可是我從來沒想過亂馬的故事也可以跟當代的跨性別議題連上關係。明明我們讀的是同一本漫畫,而我所認識的伊瑪貓,她想到的是她想成為亂馬,因為亂馬只要潑到冷水,他就可以變成女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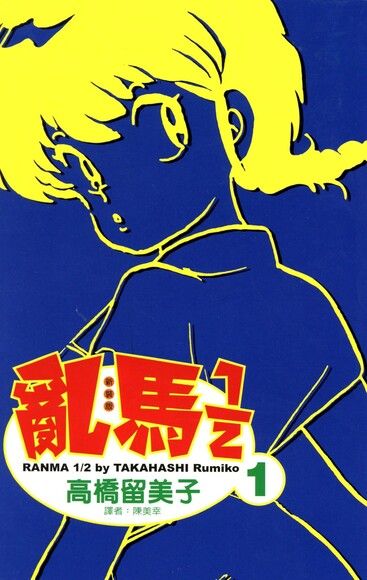
伊瑪貓是吳燕秋的伴侶,伊瑪貓在專訪裡有提到吳燕秋在很多場合,她會視情況,有時候會說你是我的男朋友,有時候會說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之所以會用「無差別格鬥派的愛情」來形容吳燕秋和她所做的事情,是因為我覺得吳燕秋是一個看起來很大剌剌的人,很豪爽、很高雄,高雄味、海港風很重的一個女人,可是其實我覺得她是一個在各種意義上,都在跟這個世界格鬥的人。你們想想她作為一個女性,她選擇成為一位跨性別者的伴侶;她作為一個女性,她選擇了一個非常邊緣的歷史學題目。
謝金魚:即使性別史跟身體史這幾年慢慢受到矚目,但到目前為止,印象中真的沒有別人敢做這個研究。我說「敢」做這個研究,意思是這還是一個非常衝擊,而且在道德上的意義非常強烈的事情。我們有一個隱形的歧視鏈。
梁秋虹:對,這是一道隱形的歧視鏈。
吳曉樂:我簡單補充一下隱形歧視鏈,我當時想說吳老師已經過世了,有沒有辦法找到其他類似的研究者,但一直碰壁。某次對方忍不住跟我說「你還搞不清楚狀況嗎?」就是剛剛講的隱形歧視鏈,你研究女性,而且是研究台灣的女性,其實是非常吃力不討好的。今天會特別告訴大家這些,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跟梁秋虹教授寫在書裡的一樣,吳燕秋當時真的是以一己之力,為我們留下了很多大家真的無法投以那麼多人生去留存的聲音。
如果我不寫的話,是不是「吳燕秋」這個詞條就消失了?
梁秋虹:吳燕秋是個一直在各種意義上格鬥的人,你看她作為跨性別者的伴侶,作為一個研究邊緣史的女性學者,以及在她人生的最後,她作為癌症的病友,她一直在跟這個世界格鬥。大家從前面的介紹應該聽得出來,我原本真的很不想要承接改寫她博士論文這個任務,因為這個任務讓我覺得非常沉重。你們可以想像你好朋友的遺作,天啊它要交到我身上,對我來說真的太沉重了。而且我是一個很懶散的人,我不喜歡一直交稿。所以我原本非常卻步,也覺得可以有更好的人選。後來我交稿之後,因為我身體有一些狀況,我準備要去動手術了,我覺得我已經在我狀況很不好的情況底下,努力改寫吳燕秋的博士論文,並且在住院前準時交稿了。我記得我們開了一場視訊會議,我還開玩笑跟吳曉樂說,我真的覺得太痛苦了,我自己的博士論文都沒有看那麼多遍!然後正當我以為結束了之後,天啊,他們居然叫我再寫一篇。
謝金魚:這是一個用生命寫的故事。
吳曉樂:好,沒有關係,因為待會我要去吃阿美了,現在大家罵我我都無所謂。老師,這我們一定要交代,我們當然知道梁教授花了非常多的心力,你要改寫好朋友的遺作,壓力非常大,因為這會決定很多人怎麼認識你朋友的研究。因為我們不可能全部都使用,篇幅跟字數大家會完全承擔不了。可是在這一切寫完之後,我們發現這樣子的話大家會很了解吳燕秋老師是誰,可是大家不曉得為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梁老師是誰。這是有原因的老師。
梁秋虹:你們當初跟我說的好像不是這樣。
吳曉樂:我們那時候就發現老師退得很後面。
謝金魚:這是一個編輯PUA現場。
梁秋虹:其實我那時候原本已經答應他們說,好,那我再另外寫一篇序言介紹吳燕秋,也介紹我跟她的關係,這樣子也許讀者比較能夠明白原作者跟改寫者的關係。但因為我一直拖稿,拖稿到我都去辦住院手續了,最後我就跟編輯說「其實我已經要住院了」。
吳曉樂:對,當時我們另外一個負責人就PO到我們的群組,然後就引起一片震撼,因為我們一直不曉得老師生病了。然後我們就說好,這篇文章我們就做到這邊為止,我們不可以再跟梁秋虹老師要求什麼東西了,要讓她好好養病。可是就在那個過程之中,老師又交稿了。
梁秋虹:對,我又交稿了,為什麼?這就是學者的宿命。我們雖然會抱怨deadline,但我們還是會交稿。在我動完手術那天晚上,麻醉退了傷口會很痛嘛,我就睡不著,然後我也不知道該做什麼。那天我在成大醫院的病房裡,一直聽到好像從隔壁病房傳來的聲音。有一位阿嬤,她整個晚上都用很淒厲的聲音一直「阿娘喂」,我原本以為她就在隔壁房,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她的病房在好幾間之外,所以你們可以想像整條長廊都能聽到阿嬤的「阿娘喂」。然後我就想說,天啊,她到底有多痛,我就突然覺得我的痛苦好像很渺小,因為我還沒有到要「阿娘喂」的地步。然後那時候,大家可以想像嘛,就是你自己生病了,外界事物的意義感都變得很薄弱,你只在乎自己而已,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刻我就突然想起了吳燕秋。
我這麼說真的不是因為我有多偉大,我真的就是突然想起她了。像我這樣一個小小的病痛,那吳燕秋在她癌末的日子裡面,她要怎麼辦呢?我有點哽咽……對,我就是想到說,其實在她癌末的日子裡,她還是一樣教書,還是一樣寫論文,然後還是一樣……因為她要維持一個正常的人生節奏。然後我就突然想起那個《牛津詞典》的故事,是不是如果我不寫的話,吳燕秋這個詞條,它就消失了……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存在這本書裡面,它會退得很後面,只是一個浮水印。然後我就覺得說,我好像不能讓它消失。

吳曉樂:好讓老師整理一下。既然老師都如此真心以對,我也講一下。要先跟各位說,我們有付給伊瑪貓老師一筆授權費,而且那個費用不低。因為我們自己的團隊,很多人都是讀到碩士,然後會一直告訴我說,其實學術研究非常辛苦,所以我們的智慧財產一定要保障夠。在支付授權費的過程中,我就突然間,因為我是一個創作者,我那時候回到家就跟我的伴侶說,如果哪一天我走了,如果有人來跟你拿我作品的授權,第一件事情你要記得收錢。再來是,我希望你知道,很多時候,我們在寫作的過程中——可能研究跟寫作很多時候是很像的,在那個過程當中你會排除你的伴侶,因為你一定要完成,你要很專注——我就跟我的伴侶說,我很多時候無法當一個很專心在你身邊的人,可是你要知道我所留下來的東西,它會以各種形式陪伴在你身邊。所以在轉這個帳的時候,我其實會想到說,原來一個人雖然物理上不在這個世界上,可是她所留下的很多東西會以各種形式,繼續陪伴她所愛的人。好,我們已經了解吳老師了,那可不可以請秋虹老師告訴我們,吳老師的主要研究內容是什麼?
研究台灣墮胎史的起點:母親的沉默
梁秋虹:我剛剛在談曉樂跟吳燕秋,她們兩人好像同樣都作為《失落詞詞典》的編輯者,大家可以把兩篇放在一起看,你就會發現,雖然她們一位是非虛構寫作的報導者,一位是做口述歷史的傳統婦女史學者,可是在她們兩人共同的成果裡——我們這本書的名字叫《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在她們兩人的作品裡,你們會看到「她們」到底是誰。「她們」其實有非常多的樣貌,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如果你把這兩篇合在一起看,你還會發現有一個世代差別。在不同歷史時期,如果你要選擇人工流產,女性會各自面臨不同的可能性與限制。比如很簡略地說,如果你是一位日治時期的女性,你能夠使用的就是中醫的漢方,而且大部分都是秘藥,這個秘藥就是把原本那些通經活血的藥物,拿來變相變成墮胎藥物。
到了戰後,戰後初期其實也沒有合適的醫療組織,你還是走三姑六婆的網絡,口耳相傳說就是要吃紅花、用黑面麻來墮胎。到了70年代之後,加上美援的國際衛生因素,有家庭計畫,有子宮內避孕器,有樂普(Lippes loop)。那時候各種避孕的手段,會跟墮胎的方式有一些重疊性。1984年之後,你有新的選擇,就是手術。1984年的《優生保健法》通過之後,它賦予了「治療性墮胎」合法化的權利,可是這個權利在誰身上?這個權利不在女性身上,這個權利其實在醫師身上。在1984年之前,如果以戰後中華民國《刑法》來說,它其實是雙罰,它既罰女性,也罰加工墮胎者。所以1984年之後,整個墮胎場域不一樣了,你會從個人性的居家用藥進入醫療機構。你在吳燕秋的作品裡會看到,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醫病關係網絡。因為吳燕秋是清華歷史所畢業,她是STS科技與社會、科技史傳統訓練出來的學生。這個網絡裡面會有什麼?它有國家、有法律、有政策、有醫師——醫師又分很多種,中醫師、西醫師、軍醫、密醫,還有藥房、助產士。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行動者網絡,最後還有技術,就是「醫療的技術」。這個醫療技術又會牽涉到很多事情,特別是牽涉到我們對於胎兒生命的認定是什麼,怎麼樣可以認定它不是一個物權,而是有法律上的人格權,它有醫療技術監控的成分在裡面。
然後在吳燕秋,我想應該是她大學時代吧,又有一個新的選項就是RU486(中止早期妊娠的藥物)。RU486大約在兩千年前後合法化。因為有RU486這種新的藥物選擇出現,才會有1997年所謂的「九月墮胎潮」,吳燕秋在大學階段經歷了被媒體大肆渲染的所謂「九月墮胎潮」。她讀的是輔大歷史系,而輔仁是一間天主教學校。所以在兩千年前後,除了我們剛剛說的國家、醫界、女性、家庭這些因素外,還有宗教,宗教團體也是當時一個非常強大的反墮胎力量。或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讓吳燕秋想去做這個題目。
可是我覺得這些都是很表面的因素,其實還有一個很深層的因素,就是她研究的起點。她研究的起點是什麼?她研究的起點就是「母親的沉默」。我們的上一代都是非常多產的家庭,這跟避孕技術的普及化和可及性有關。吳燕秋的母親有六個小孩,她就很好奇她的母親有沒有墮胎過,可是她發現每次問母親這個問題,母親都沉默,閉口不答,怎麼樣都問不出來。你們可以想像她的挫折嗎?我作為一個婦女史的學者,我從我自己母親身上居然問不出來。但微妙的是,儘管她母親一直對這件事情保持沉默,可是在她尋找口述歷史訪談對象時,都是她媽媽在幫忙。你要知道吳燕秋的受訪者都是1920年出生的長輩,是上一代,我們母親、我們祖母輩的人,她要怎麼尋找、怎麼樣讓這些受訪者願意開口?她透過她母親幫忙介紹。媽媽透過傳統的社會網絡,媽媽努力在後面幫她奔走。我覺得媽媽的心理很微妙,有些事,媽媽不想說,但是會找認識的朋友來說。我覺得這是吳燕秋研究的初衷跟起點。
在「生命權」和「選擇權」之間,賦予歷史的觀點
梁秋虹:那吳燕秋研究的貢獻是什麼?其實一直到現在,關於人工流產這件事情,依然存在所謂的「胚胎生命權」,跟女性的「生育自主權」或是說「生育選擇權」這兩大辯論。吳燕秋她不是在跟你辯論女性主義上的對與錯、哲學或倫理上的政治正確或倫理價值判斷,她其實是從歷史的觀點來回答,這兩件事情到底是什麼。所謂的「胚胎生命權」就關係到說,到底什麼是生命?我們怎麼樣認識生命?吳燕秋的研究告訴我們,雖然大家都很反對墮胎這個說法,但其實大家反對的是「墮」,並不是「胎」,因為在傳統中醫的觀念裡,胎其實是一個很中性的名詞。傳統上,比如說《清律》,如果墮胎罪要成立,那個叫鬬毆而致人……
謝金魚:就是如果你傷害了這個孕婦,那是因為你傷害了孕婦,所以法律上有刑罰,罰的是傷害孕婦本人,而不是因為傷害胎。在過去的法律當中,胎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人格。
梁秋虹:在《清律》裡面,胎怎麼樣才被視為是生命?就是它要初具人形,所以其實要等到你落產以後,初具人形,它才被視為生命。那怎麼感受到胎呢?誰來界定?以前又沒有子宮超音波,也沒有辦法做任何檢測,所以以前是誰來認定呢?就是母親啊。母親感受到胎動的那一刻,胎就成立了。可是在西方醫學引進台灣之後,就開始有了不同的概念。胎兒為什麼有生命權?比如說受精卵的概念,其實是在醫學的檢測技術上,我們要知道它著床了,它受精、它著床,或是你透過賀爾蒙變化等檢驗出來。現在美國跟歐洲對於人工流產的法律態度走向兩極,歐洲朝向開放,美國轉向限縮。比如美國德州的《心跳法》(Heartbeat Bill)。《心跳法》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你懷孕六週以上,胎兒一旦有了心跳,它就有生命。而且以前是透過《刑法》來罪罰化,那美國的做法是任何人都可以主張民事訴訟,所以訴訟打起來就是沒完沒了,什麼人都可以告。
在所謂胎的生命權上,你可以看到一個歷史觀點的演進。那在法律上面呢?吳燕秋會告訴你,你以為傳統很落後嗎?其實傳統不見得有我們想像得那麼落後,因為在傳統中國法的系譜裡,其實它是主張母體優先。從《公主之死》的例子可以看到,雖然以前的法律會有一些「法不入家門」等規定,但它是母體優先,優先保障母親的生命安全,它並不會直接處罰母親。可是在日本的近代刑法引進台灣之後,墮胎罪開始成立。法律懲罰誰?法律懲罰的是選擇墮胎的女性。戰後的《中華民國刑法》就繼承了這套系統,《中華民國刑法》比日本刑法又多了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它雙罰。雙罰是什麼意思?就是我既懲罰墮胎的女性,我也懲罰幫你墮胎的人,就是所謂的「加工墮胎罪」。一直到戰後,大概1980年代前期都是雙罰。這種法律上的限制導致女性不得不在一個非常隱秘、非法、不安全的狀態底下,她要自己去想辦法墮胎,不能讓人家知道,因為這在法律上是要被處罰的,而且是刑事上面的處罰。
那這個情況到什麼時候改變呢?就是1984年的《優生保健法》。它是讓醫師出來做判斷,不是母親喔,是醫師出來做判斷。為什麼?因為它只讓治療性的墮胎合法化。像我們現在衛福部關於人工流產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到真正透明的數字,都是所謂的治療性流產的數字,檯面下的黑數其實都是看不見的。另外1984年《優生保健法》還有一個法律上的全新發明,就是配偶同意權。其實配偶同意權在法律上是一個近代的發明,女性要執行墮胎,已婚婦女必須要取得配偶的同意權;如果是未成年的話,就要取得家長的同意權。2022年台灣《生育保健法》的草案,就在爭執要不要廢掉配偶同意權。但是要廢掉配偶同意權不容易喔,在座的男性朋友,你們應該心裡也會有一些想法。而且最近還牽涉到一個更新的議題,當人工生殖有代孕的需求,也有自然流產的問題。
吳燕秋就是從歷史的觀點告訴我們,你如果把胎兒的生命權跟女性的生育自主權當成一個哲學問題、道德問題、價值問題討論,你可以選擇各自的立場;但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切入,你可以看到很多跟我們原本想像不同的事情。吳燕秋除了在這兩個觀點的拔河之間,賦予一個歷史的觀點之外,她也告訴你,其實事情從來都不是我們想像得那麼簡單。事情從來都不是只有女人跟她的子宮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已。還有什麼呢?有國家父權,有法律跟政策,有家庭父權,有家父長的同意制,然後涉及到比如說你的父親、你的丈夫,他對這件事情是不是有法律上的權利?有醫療上面的權利?有各式各樣我們所想像的東西,一層一層地加諸在女性身上。我們以為女性可以做選擇,可是在我們選擇之前,其實被加諸了層層限制,你的子宮從來都不是你的子宮,它被很多的人事物共同監管著。

詞彙的政治性:離不開婚與家的「婦女」vs「女性」
梁秋虹:作為一個改寫者,我改寫程度最多的地方,其實是口述歷史的部分。我有兩個用意,第一個用意是,我覺得直接去摘錄口述歷史,大家可以聽到吳燕秋的聲音。因為我在裡面不只節錄了受訪者的聲音,也包含了訪問者的聲音,所以你們會看到很多括號,或者說吳燕秋怎麼樣去問問題,裡面有吳燕秋的口氣。另一個用意是,我把這些口述歷史節錄在吳燕秋的論述後面,讀者可以去對照。因為對於事情的判斷從來都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我們不能夠只看學者的研究成果的聲音,我們也應該要去看看其他聲音,看這個學者的說法、論點是不是可以成立。因為受訪者不會只有一個,特別是吳燕秋受訪者的特色,她不只訪問女性,她也訪問很多男性,她訪問醫師、助產士、密醫、軍醫,訪問各式各樣的藥商、藥房的經營者等等,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聲音跟聲音之間的關係。
那我作為改寫者,除了做這件事情之外,其實我還偷偷做了一件事,但我想大部分的人應該看不大出來,就是,吳燕秋她畢竟還是一個在傳統婦女史訓練底下的學者,所以她的原文大部分使用的字眼都是「婦女」。我們又回到《牛津英語詞典》的故事,其實詞語是充滿政治的,我們怎樣去定義它,命名它,發現它,指明它。為什麼吳燕秋都是用「婦女」呢?這就跟謝金魚前面講的有關,就是女人這個身分在歷史學這個領域,尤其是婦女史的領域出現的時候,她離不開婚姻跟家庭,她離不開她的父親跟丈夫,她被依附在婚姻跟家庭場域裡面。後來我就把「婦女」這個詞換成了「女性」。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考慮到婦女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比如說「未成年」的女性、在「非婚生」的前提底下孕產的女性,甚至是人工生殖的環境底下自然流產的女性,都應該被放進「女性」的範疇。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最近學生給我的回饋。我在成大開性別史的課,最近有學生跟我說,「老師,我覺得讀性別史啊,有一種歷史的驚奇和痛苦」。他們覺得「天啊,怎麼這些事情我以前從來都不知道?」可是在驚奇的同時,又同時讓人感到痛苦。因為有些事情不知道其實比較快樂,反而知道之後就會變得好沉重。比如在場這位男性朋友他可能回去就想說,我是不是應該要支持或反對配偶同意權?你就會開始反思很多事情。那到學期末的時候,就有一個男學生跟我說,對於這種驚奇跟痛苦的感覺,他覺得難以平衡。然後對於女性主義理論,他也不是很確定作為一名生理男性,他到底能夠成為一位女性主義者到什麼程度。我就跟他說:「把女性主義忘掉吧!把這種為了他人而痛苦的感受留下來,因為這表示你心中還有善良,你才會感到痛苦,像我現在就不太會感到痛苦了(笑)」。希望今天來到分享會的大家,能夠記住一位女學者,她在這個研究過程當中,她帶給你們的驚奇跟痛苦。謝謝大家。
吳曉樂:我們上一場活動在高雄,與談人是〈最小公倍數〉的作者張嘉真,我們兩人都是讀台大的,我讀台大已經是20年前,當時我們的性別學程叫做婦女學程,那學生就不想修了,會覺得我才18歲,我要去修一個婦女學程。但那時候我知道如果要學女性主義,我只有在婦女學程才找得到,不然一開始我也是很有扞格。那時候我還跟教授說,為什麼我們學的東西一定要叫婦女?教授說,因為我們目前主要的觀點,以2006年來講,其實還是著重在婚姻,我們看見女性,但我們還是著重在有婚家的女性。而且重點是到現在都還沒有改,嘉真說她也有去修這個婦女學程。
梁秋虹:這給我一個靈感,不然我們來開一個少女學程。
吳曉樂:對啊!18歲去修個婦女學程。
謝金魚:沒有沒有,真正的少女會覺得我才不要上什麼少女學程,就像什麼青春什麼的,都是我們這種不青春的人。
回覆給我們想做的無非是,留住「對女人有愛」的詞條(下) – 游擊文化 取消回覆